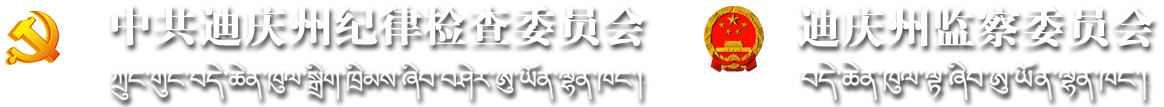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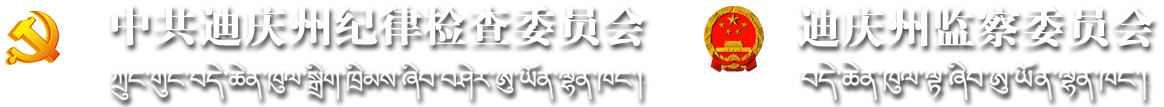
以案明纪释法 |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相关问题辨析
以案明纪释法 | 准确识别以定向增发股份收益权为工具的利益输送
以案明纪释法 | 区分不同情况准确认定低价购房行为性质
以案明纪释法 | 医药产品采购中收受销售方财物构成何罪
以案明纪释法丨准确认定挪用公款给“一人公司”使用的行为性质
以案明纪释法丨准确识别以“咨询服务费”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
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其近亲属以出资购买请托人提供的拟上市公司股份为幌子,并以股份预期增值利益作为标的接受利益输送,虽其行为隐蔽复杂,但究其本质仍是权钱交易。笔者认为,重点可以从国家工作人员有无接受行贿人请托利用职权为其谋利、依托职权还是市场获取股权、是否承担市场风险等方面,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研判,精准识别以出资购买原始股为名收受贿赂行为的权钱交易本质。
以案明纪释法丨村干部在拆迁工作中侵占补偿款的行为性质分析
准确识别以“商业机会”为幌子的权钱交易
查证钱款去向系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重要内容,对于监察机关在调查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的“自洗钱”问题以及检察机关在监察机关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存在“自洗钱”问题时,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如何衔接?笔者结合案例,从监察调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分别发现“自洗钱”问题时在管辖及线索移转、证据的收集与使用、涉嫌“自洗钱”犯罪的审查起诉等方面的监检程序衔接问题进行分析,以资参考。